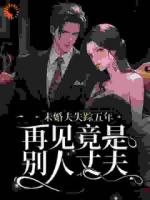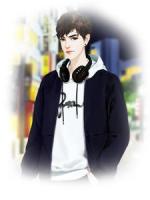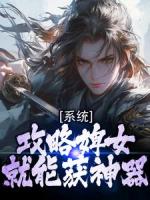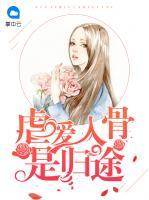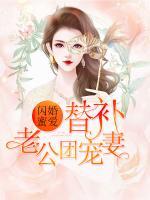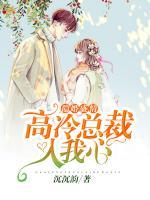2
签过合同,我搬进“新家”。
我这一天实在倒霉,上午喝水呛到,下午不慎将钥匙扔进垃圾桶,忙进忙出,终于安置下来。
夜晚降临,楼上楼下飘来饭菜香味,我打包一份炒饭,打开电视边看边吃。
其实我根本不爱看电视,但屋里太静悄悄,开电视纯粹图个热闹。
黄金时段,各大卫视被仙剑三攻占,一帧帧一画画,尽是徐长卿与紫萱的三世情缘。
两人袒露毕心迹,各自掬一捧忘情水,我正猜测他们是否甘心饮下,忽然电视发出滋滋声响。紧接着,屏幕乍暗灯光熄灭,整个房间猝然陷入黑暗!
停电了?
那一瞬间我甚至生出找座寺庙上柱香的想法,人究竟能倒霉到什么程度,我不想进一步体验。然不待我作出任何应对措施,下一刻,仿佛买一赠N,客厅,厨房,就连我不曾打开的卧室,都齐齐亮起灯光!
这还不够,老天甚至友情赠送一出大变活人——
只见正对面处,立着一道高高瘦瘦,肩宽腰窄的身影。
我张了张口,却在视线触及到对方的那张脸时,陷入不可置信。
眼前人眉是眉眼是眼,起势凌厉,末了却勾出一抹柔情;鼻梁很高,侧脸轮廓分明,是干净利落的英俊长相。
这张脸我再熟悉不过,它出现在《冬》的作者介绍处,旁附小字:摄于1994年秋。
是徐朔,本人比照片还要好看,可见采访中提到的不上相并非玩笑。
我不由愣住,分明父母离异随处可见,怎么到我这里就产生幻觉了?未等我持续恍惚,徐朔警惕道:“你是谁?”
嗓音低沉带一丝哑,我陡然清醒。
我右手还握着筷子,向下一瞥却发现桌上的饭盒不翼而飞。
再仔细看,桌还是那张桌,上面却多了张桌布。
我环顾四周,熟悉又陌生,熟悉的是格局,陌生的是边边角角。
这里门后有挂饰,阳台有花盆,盆里正开着花。
一眼便知,主人比我讲究许多。
我心念电转恍然大悟,原来凭空冒出的不是徐朔,而是我自己!
信息量太大,塞得我脑袋卡壳。
我沉默十几秒,迎上徐朔的质问:“我是蒋乐。”语毕灵感突至,又补上,“我很喜欢你的《冬》。”
徐朔仍旧警惕:“你怎么在我家?”
我心说我也想知道,“其实我来自十几年后。”
徐朔“噢”一声,“新骗术?听起来挺傻的,有待改进。”
“我不是骗子,”我强压下心头的震撼,努力解释:“我也租了这套房子,今天——2009年7月11日刚搬进来的。晚上七点半左右屋里突然断电,断了大概有十秒,电来的那一瞬,我就在这里了。”
还把停电圆进去了,徐朔想,继而无动于衷道,“继续编,编完了我们去警察局。”
“我真的不是骗子,”我头痛,“现在是什么时候?几几年几月几号?”
“1997年5月30日。”
我脱口而出:“7月1日香港回归!”
“这算是预言吗?”徐朔被逗笑,“电视里天天播,喏。”他侧开身,我才发觉屋里还开着电视,只不过被静音。
临近回归,电视里时不时插播相关消息,新闻频道更甚。我凝神盯着电视,“五月三十,”我小声重复一遍,就在徐朔即将失去耐心时,我蓦地提高声音,“我知道怎么证明自己了!”
“还有二十分钟,新闻会宣告‘桑梓路失踪案’被警方破获!”
这起案件在当地可谓是无人不知。
八百来米的一条路,连续三天失踪五人。
案子初发时警方便设立专门小组,然一拖数月,悬而未决,案子就此沦为悬案。
终于在1997年5月,当年负责此案的老刑警抽丝剥茧,将罪犯绳之以法。
消息一出,引发巨大轰动。
我小时候听大人们当故事说过,长大后翻看地方书报,又见过几回。
因为犯罪性质严重、所隔年代不远、案发地离自己仅有几公里,我将案子的来龙去脉记得清清楚楚,其中包括宣破时间:八点十分。
徐朔点头,“可以。”
这二十分钟在两人的无声对峙中过得尤为漫长。
八点九分,我盯着屏幕眼也不眨;八点十分,当播音员念出“桑梓路失踪案”时,我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与此同时,徐朔卸下大半防备。
“我相信你。”他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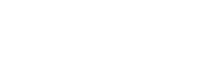
 已完结
已完结